东北一枝花
-张哈哈
0:00 /
0:00
(朗诵:)
12
播放列表
-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镇高家村)人,后入籍钱塘(今浙江杭州)。高士奇早年家贫,后在詹事府做记录官。康熙十五年(1676年)升为内阁中书,领六品俸薪,住在赏赐给他的西安门内。 高士奇每日为康熙帝讲书释疑,评析书画,极得信任。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晚年又特授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死后,被追谥文恪。他平生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著有《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地名考略》、《清吟堂全集》等。

猜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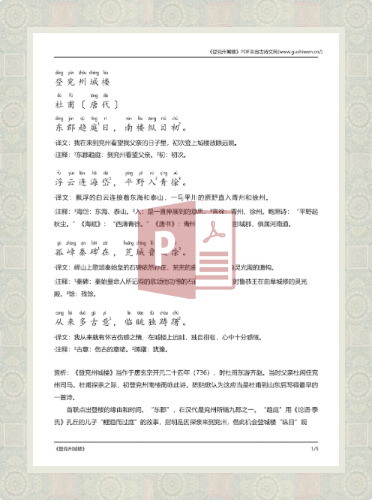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