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一枝花
-张哈哈
0:00 /
0:00
(朗诵:)
12
播放列表
-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河梁与子一携手,云在高天雁横斗。空江日落无素书,千里风尘隔杯酒。
忆昔避兵秦溪傍,渔舟八口同仓黄。荒山橡栗饥戴釜,淫雨泥涂足裹创。
我家兄弟半存亡,枯鱼泪尽天茫茫。嗟我君子忧高堂,袱被翻然归故乡。
欲留不留扁舟去,欲别不别临歧语。踯躅悲歌《惜晤》篇,六年江海各烽烟。
渔人桃花隔蛮洞,蜀帝炎荒叫杜鹃。钟山伐遍孝陵柏,史本窜尽思宗编。
君卧朴巢长却扫,搜诗自订三唐稿。义熙处士一陶潜,同谷哀歌惟杜老。
我行度岭虔台去,肠断先臣尽忠处。介推绵上只余灰,徐孺南州少遗絮。
天涯踪迹断浮萍,匿影枯桑息倦翎。忽枉故人双鲤讯,挑镫字照三秋萤。
君今四十能高举,羡尔鸿妻佐舂杵。为儿事亲之日长,有母此身未敢许。
贞松堂上青扶疏,不受秦官五大夫。春风药阑雪寒牖,羡君乐事无不有。
沈酣千日乱离年,花月七言文字友。鄙人东海望清光,目送南鸿一搔首。
尺书为我报相思,遥折梅花为君寿。

猜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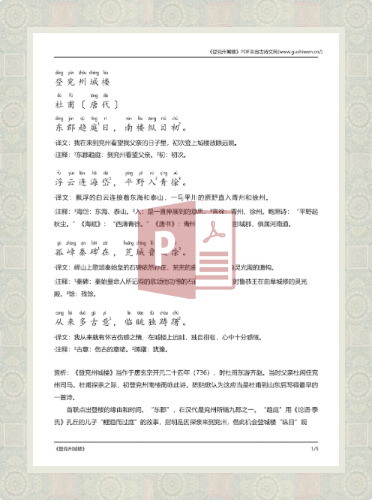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