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右,臣准阁门告报,蒙恩授臣中书舍人者。窃以唐虞三代之君,兴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际,所以播告天下,训齐百工,必有诏号令命之文,达其施为建立之意。皆择当时聪明隽乂、工于言语文学之臣,使之敷扬演畅,被于简册。以行之四方,垂之万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谋谟访问,三盘五诰誓命之书,刻之为经。后世学者得而宗之,师生相传,为载籍首。吟诵寻绎,以求其旧。一有发明,皆为世教。盖其大体所系如此。
逮至汉兴,虽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诰令下者,典正谨严,尚为近古。自斯已后,岂独彝伦秕,其推而行之,载于明命,亦皆文字浅陋,无可观采。唐之文章尝盛矣。当时之士,若常衮、杨炎、元稹之属,号能为训辞,今其文尚存,亦未有远过人者。然则号令文采,自汉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缺欤?
伏惟陛下以天纵之圣,阐明道术,所以作则垂宪,纪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汉唐。至于出口肆笔,发为德音,固已独造精微,不可穷测。则于代言之任,岂易属人?臣浅薄暗瞀,学朽材下,误蒙陛下知之于摈排忌疾之中,收之于弃捐流落之地,属之史事,已惧瘝官。至于推度圣意,讨论润色,以次为谟训彰示海内,兹事至大,岂臣所堪?况侍从之官,实备顾问,而臣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岂独施于翰墨,惧非其任。至于谋猷献纳,尤不逮人。伏望博选于朝,旁及疏远,必有殊绝特出之材,能副圣神奖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赐寝罢。
张孝先曰:中书舍人掌诏诰乃代言之任,其职未易居也。子固推之于唐虞三代以迄汉唐,而言居是职者之渐不及古,其议论卓然不刊。盖非子固不足以称斯任也。后世诏告之文,岂独不能比盛唐虞三代,即汉之深厚尔雅者,且邈乎其绝响矣。
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猜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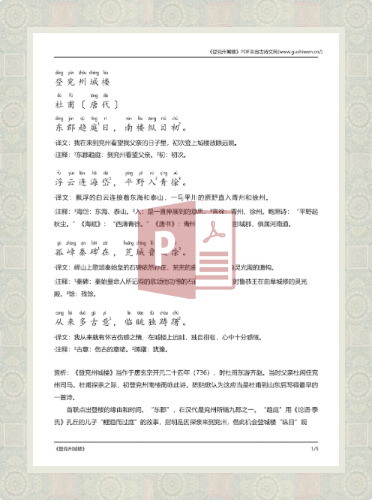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