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心则通知,人于手则窒,手则合知,反于神则离。知所取于其前,知所识于其后。达之于不可迕,知度而有度。天机阖辟,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论书如是,吾闻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书之人自东晋王羲之,至今且千余载,其中可数者,或数十年一人,或数百年一人。自明董尚书其昌死,今知人焉。非知为书者也,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也。”
禹卿作堂于所居之北,将为之名。一日,得尚书书“快雨堂”旧匾,喜甚,乃悬之堂内,而遗得丧,忘寒异,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或誉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鸟鷇而食,成翼而飞,知所于劝,其天与之耶?虽然,俟其时而后化。今禹卿之于尚书,其书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为之记,以待世有识者论定焉。
译文
“心领神会了,写于手下却显得滞塞;手下貌似相合了,却反倒和神分离了。在书写之前无所取法,在写后又无所标志。通达于不可乖迕,没有法度却又有法度。天机有开合,而我却不明白其中的原故。”禹卿论述书法如上,我听了认为他说得好。禹卿又说:“书法的艺术从东晋王羲之开始,到今天已经将近一千年了,其间可以称得上是书法家的,或者几十年出一位,或者几百年出一位。自从明朝董尚书董其昌死后,直至今天还没有书法家出现。不是没有搞书法的人,只是勤于练书法的人没有高的见识,而精于了悟的人在书法中又不能表现出来。”
禹卿在居所的北面建了一个堂屋,想要给它起个名字。有一天,他得到一块董
“快雨堂”本是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一块匾额。作者的朋友王禹卿在自己住所之北新筑一堂,作为练习书法之所在,想寻求一个较有寄寓而又合于此堂实际的堂名,一日,得到董其昌题写的这块旧匾,大概是觉得合乎书法家在行笔快意累累时,手底会笔墨淋漓,以致让人感到满堂风雨不胜寒。于是非常高兴,便悬之于堂,借以为名,然后则“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作者不由十分感慨,作了这篇《快雨堂记》。
参考资料:完善
《快雨堂记》是一篇散文。这篇散文虽是记快雨堂,却纯以议论出之,篇幅不长,写得舒迂徐缓。前半部分引王文治的论书之语,不厌其繁;后半部分写王筑堂得匾,日夜临池的事,仅用寥寥数语,人物的形象却已跃然纸上。此文运用比喻生动而富有寓意,使用问句令文气跌宕,读来唱叹有致,文有尽而味无穷。
姚鼐在《与王铁夫书》中说:“文章之境,最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至晚年,在《稼田集序》中又进而指出:“文者,皆人之言书之纸上者尔!在乎当理切事,而不在乎华辞。”因而主张以干淡自然作为衡量文章的最高标准,这篇散文则体现着这样一种艺术追求。
文章开篇并不似一般杂记体文章那样先交代作记缘由,或描写堂奥本身的建筑、环境、求记者的寄托。而是记叙了堂主王禹卿论书法的两段话,指出书法艺术之难,便难在于心手相应,手与神合。自王羲之至今,干余年中,著名书法家甚少;而自明代大师董其昌之后,书坛则无人,原因都在于此,“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书法造诣也就难达此境界。
姚鼐(nài)(1731~1815)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任礼部主事、四库全书纂修官等,年才四十,辞官南归,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江南紫阳、南京钟山等地书院四十多年。著有《惜抱轩全集》等,曾编选《古文辞类纂》。

猜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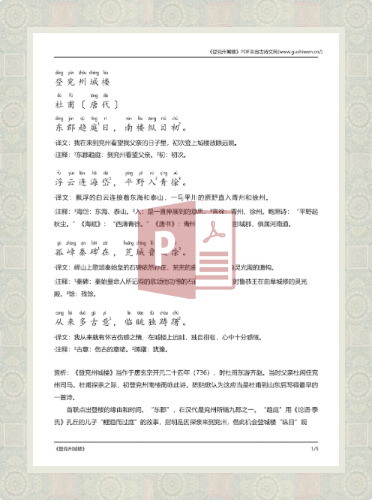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