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译文
自从遭贬获罪,我居住在这个州郡,内心始终满是惶恐不安。但凡有闲暇,我便悠然漫步,无拘无束地四处遨游。平日里,我常与友人一同攀高山、探深林,一直走到蜿蜒溪流的尽头。那些偏僻的清泉、奇特的山石,凡是偏远之地,我们无所不至。抵达目的地后,我们拨开杂草席地而坐,倾尽壶中酒,一醉方休。醉后便相互枕靠着入眠,梦中总会奔赴心中向往的美好境地。睡醒了就起身,起身便踏上归途。我原以为这州里所有形态奇特的山峦,我都已游历殆尽,却从未知晓西山竟如此奇绝独特。
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闲坐法华寺西亭,远眺西山时,才忽然指着它惊觉其奇特之处。于是吩咐仆人渡过湘江,顺着染溪前行,
一、古今异义
①未始
古义:未尝,从来没有 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义:没开始
②累积
古义:重叠、积压 攒蹙累积。
今义:积累
③然后
古义:这样以后 然后知吾向之末始游。
今义:连词,表示接着某种动作或情况之后
④于是
古义:从此,从这时 游于是乎始。
今义:连词,表示后事紧接着前一事
⑤更
古义:动词,更换交替。 醉则更相枕以卧。
今义:程度副词,更加。
⑥披
古义:拨,拨开。 到则披
《始得西山宴游记》的灵魂全在“始得”二字,无论是立意的深浅还是布局的巧思,都围绕这两个字层层展开,全文五次或明或暗的点题,让“始得”成为贯穿全文的核心脉络。文章以“发现西山—宴游西山—感悟西山”为线索自然分为两段,每一处内容都紧扣“始得”的意蕴,既写宴游经过,更藏心境变迁。
第一段重在铺垫“始得”之前的状态,为西山的登场蓄势。作者以“僇人”自陈,点明被贬永州的特殊身份,用“恒惴僳”三字道尽贬谪后的惊恐不安——这份积压已久的屈辱、压抑与抱负难伸的苦闷,让他的游山玩水与寻常士大夫的闲情逸致截然不同。他并非为赏景而游,而是想借漫游排解忧愤、忘却现实,在精神上寻找寄托。文中“
这篇作品以“始得西山宴游记”为题,艺术表达精妙独到,既在构思与选材上匠心独运,又以多样手法寄托深沉情志,尽显柳宗元贬谪后的心境与才情。
选材立意独出机杼,精准扣合“始得”题眼。全文看似对西山着墨不多,实则字字皆为西山铺垫——柳宗元谪居永州的特殊境遇,让他既有闲暇漫游,又心怀贬谪的忧懑,这份复杂心绪为全文奠定了悲凉底色。他平日的游览本就带着宣泄排遣的意味,“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尽显随意无目的;“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后相枕而卧、觉而起、起而归”的状态,更是苦中觅乐的散漫任性。而这些铺垫,都只为反衬初见西山时的震撼。就连寻道登山的艰难过程,作者也仅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革新运动,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被贬到永州担任司马。到永州后,其母病故,王叔文被处死,心情压抑。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这篇文章便是这一时期所作,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
参考资料:完善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一篇散文,为《永州八记》的第一篇。全文共分两段,第一段写作者始游西山时的心情及对西山景色总的评价:怪特;第二段正面写游西山的情景,这部分紧紧围绕着“始”字展开。全文语言清丽,结构完整,情景融为一体,写景重在写意,抒情深沉而含蓄,抒发了作者对其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现实丑恶的无奈之情。
柳宗元(773年~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人,出身河东柳氏,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被贬永州期间,居所附近有愚溪,人称“柳愚溪”。后官终柳州刺史,世人称“柳柳州”。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章的成就大于诗作。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被推为“游记之祖”。著有《河东先生集》。

猜您喜欢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
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
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洛阳才子谪湘川,元礼同舟月下仙。
记得长安还欲笑,不知何处是西天。
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
醉客满船歌白苎,不知霜露入秋衣。
帝子潇湘去不还,空馀秋草洞庭间。
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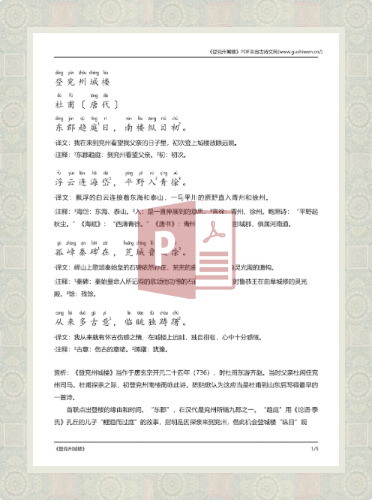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