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我本江海客,风水性所谙。争食雁鹜侣,眠卧蛟龙潭。
吴山及越水,到处工幽探。强来北地游,埃壒积不堪。
佣书读中秘,逐队趋じ𧽼。烟海迷津涯,十不忆二三。
欲投祭酒笔,骨相惭燕颔。平慈亲迫榆景,发脱难胜簪。
迎养薪桂地,所愧旨甘。斜街路南头,因树三闲庵。
老人弄孙罢,绣佛依香龛。昨来秋风起,语我思江南。
片舸下泽潞,家具不满担。拜送心断绝,而我羁归骖。
有儿名一生,废学增痴憨。曾不识之无,但索梨与柑。
有女已上头,长欲与母参。心性稍黠慧,恨渠不为男。
俯仰既无藉,出处弥自惭。薄游向齐岱,聊写忧心惔。
一看封中云,快听海上谈。悬车待春发,陟岳搜穹嵁。
日观俯沧海,天门豁层岚。扪碑倚石表,发策开玉函。
谁知灵威丈,赫尔嗔其贪。仍复驱我来,卧病同僵蚕。
努力近药物,割嗜疏酒甔。二竖杂虚耗,环伺何耽耽。
昔年壮意气,万象供嘲唅。今如病马伏,不任驱骖驔。
面用方曲障,口拟石阙含。亦有旧携剑,锈涩昏星镡。
亦有幼读书,尘封饱鱼蟫。一仆穷相随,肤皱鬓𣰦毵。
作字遣之卖,易菜日半篮。缩颈向炉火,暖意偷春酣。
忽讶岁云尽,泪下衿衫渰。转忆去年夕,浑含谈诂諵。
索逋虽填门,相对乐亦湛。今反作孤客,枯寂同瞿昙。
百感自然集,苦吟讵所耽。顾影坐分岁,渐听晨钟韽。
黄景仁(1749~1783),清代诗人。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四岁而孤,家境清贫,少年时即负诗名,为谋生计,曾四方奔波。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后授县丞,未及补官即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年仅35岁。诗负盛名,为“毗陵七子”之一。诗学李白,所作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怀,也有愤世嫉俗的篇章。七言诗极有特色。亦能词。著有《两当轩全集》。

猜您喜欢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许可,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将四条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而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既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神鬼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见识。为天下计,则必已饥已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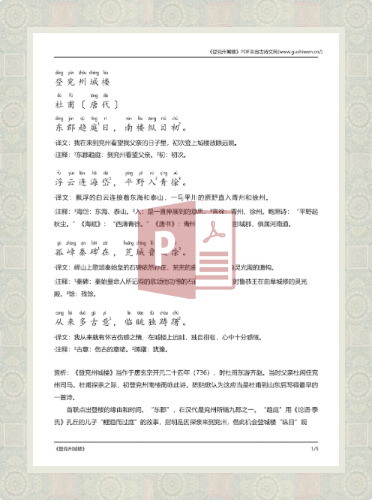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