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臣闻之,“士之有耻,犹国有耻也”。今朝廷之上,多畏谨之士,少敢言之臣。夫畏谨之士,固可以保身,而不足以济事。敢言者,非好为讦直也,盖以国家之利害,不可以不辨;邪正之得失,不可以不明。今陛下有励臣之道,而臣未有以报陛下者,臣窃耻之。
夫赏罚者,人主之所以励臣也。赏以劝善,罚以惩恶,此古今之通义也。今朝廷之赏罚,可谓明矣。然而士之受赏者,未必皆善;受罚者,未必皆恶。何则?赏罚之柄,一出于上,而臣下之能否,不得自见也。故赏罚虽明,而不足以励臣。
臣愿陛下明诏大臣,使各举其属,以能否为黜陟。然后陛下亲加考察,而赏罚随之。如此,则人知自勉,而不敢为欺。又诏侍从、台谏,各举所知,以为监司、郡守。然后陛下亲加考察,而黜陟随之。如此,则人知自重,而不敢为非。
夫监司、郡守,民之师帅也。监司正则郡守不敢不正,郡守正则县令不敢不正。县令正,则民自安矣。今监司、郡守,多不得人。非才不足以胜任,而心有所畏也。畏陛下之法,而不畏天下之民。故宁违陛下之法,而不敢违宰相之命。宰相之命,未必皆善也。而监司、郡守,不敢违之,何也?畏宰相之权也。
臣愿陛下重监司之权,而轻宰相之权。监司得自举郡守,郡守得自举县令。然后陛下亲加考察,而赏罚随之。如此,则人知所畏,而不敢为非。又诏宰相,不得自用台谏。台谏得自举属官,而陛下亲加考察,而赏罚随之。如此,则人知所畏,而不敢为欺。
夫台谏者,天子之耳目也。台谏得人,则天子之耳目明;台谏不得人,则天子之耳目蔽。今台谏多不得人,非才不足以胜任,而心有所畏也。畏宰相之权,而不畏陛下之法。故宁违陛下之法,而不敢违宰相之命。宰相之命,未必皆善也。而台谏不敢违之,何也?畏宰相之权也。
臣愿陛下重台谏之权,而轻宰相之权。台谏得自举属官,而陛下亲加考察,而赏罚随之。如此,则人知所畏,而不敢为非。又诏宰相,不得自用侍从。侍从得自举属官,而陛下亲加考察,而赏罚随之。如此,则人知所畏,而不敢为欺。
夫侍从者,天子之股肱也。侍从得人,则天子之股肱强;侍从不得人,则天子之股肱弱。今侍从多不得人,非才不足以胜任,而心有所畏也。畏宰相之权,而不畏陛下之法。故宁违陛下之法,而不敢违宰相之命。宰相之命,未必皆善也。而侍从不敢违之,何也?畏宰相之权也。
臣愿陛下重侍从之权,而轻宰相之权。侍从得自举属官,而陛下亲加考察,而赏罚随之。如此,则人知所畏,而不敢为非。
夫宰相者,天子之腹心也。宰相得人,则天子之腹心实;宰相不得人,则天子之腹心虚。今宰相多不得人,非才不足以胜任,而心有所畏也。畏陛下之法,而不畏天下之民。故宁违陛下之法,而不敢违宰相之命。宰相之命,未必皆善也。而宰相不敢违之,何也?畏陛下之法也。
臣愿陛下重宰相之权,而轻陛下之法。宰相得自举属官,而陛下亲加考察,而赏罚随之。如此,则人知所畏,而不敢为非。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改名陈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孝宗淳熙五年,诣阙上书论国事。后曾两次被诬入狱。绍熙四年光宗策进士第一,状元。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公事,未行而卒,谥号文毅。所作政论气势纵横,词作豪放,有《龙川文集》《龙川词》,宋史有传。

猜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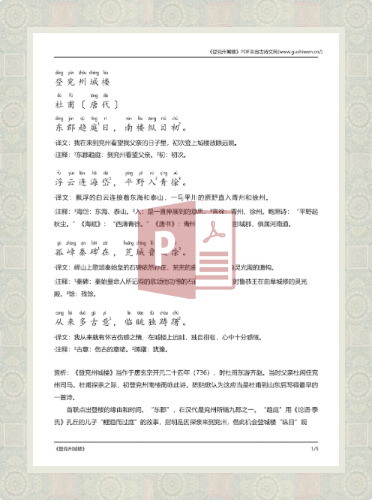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