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少时轻离别,志气誇壮强。及玆未莫年,巳复多感伤。
念昔之蜀都,执经侍贤王。放怀礼法地,取乐文翰场。
耆俊满大廷,济济会冠裳。出言有同趣,讲艺靡乖方。
惟王帝室英,聪达世莫当。精诚洞千古,一目连十行。
道大才更雄,气温色弥庄。劳心抚庶政,虚巳思虞唐。
封内数十州,德声蔼洋洋。皇天䧏嘉贶,百谷屡丰穰。
盛美不自居,检身循典章。凝情观众妙,博问取所长。
自惭鲁钝学,三岁承宠光。避席玉座侧,设醴金殿旁。
睿哲能兼容,阙失专覆藏。采陟等葑菲,比珍匪琳琅。
近者迎属车,拜辞褒水阳。情真赐色笑,感激铭肺肠。
喜遇大比秋,斋官含昼凉。寸情拟披豁,古训思对扬。
虽乏㳙埃𥙷,忠贞誓无忘。岂知事难必,曩愿弗获偿。
徵书京国来,迅若晨风翔。谬忝较文职,守臣启储皇。
储皇新德政,出令闻八荒。戒饰况丁宁,庸薄实恐惶。
经旬废寝食,呕欬病在床。王人俄继至,币自藩阃将。
强起扶杖迎,坐语两徬徨。报国固臣节,效信亦士常。
趋召违天朝,惧非义所臧。王心秉忠孝,处事明且详。
微衷倘见察,庶或贷死亡。赫赫我大明,幅员同夏商。
仁恩洽宇宙,帝业炽以昌。九有如一家,内外咸乐康。
取士皆为国,何尝限封疆。蜀道平若砥,汉水浅可航。
胡为不能往,矫首徒慨慷。白日流光辉,葵藿随低昂。
愿王崇明德,以慰葵藿望。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朱棣杀害。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

猜您喜欢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当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须花下眠。
花前花后日复日,酒醉酒醒年复年。
不愿鞠躬车马前,但愿老死花酒间。
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世人笑我忒疯颠,我咲世人看不穿。
记得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作田。(原版)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版本一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来花下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花酒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风骚,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作田。版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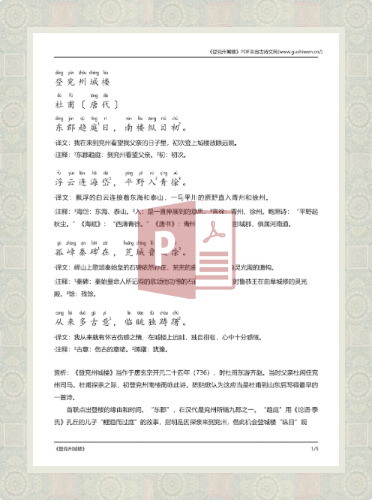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