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译文
细密的雨丝没能聚成雨珠,映在澄澈的天空中,显得若有若无。
花萼上时常凝结着水珠,滚动流转,恰似颗颗圆润的明珠。
宛如美人洗去脂粉,清雅的香气在洁白的花瓣间萦绕。
黄昏时分,氛围愈发清寂,缀满水珠的花朵沉甸甸的,仿佛需要人搀扶。
想来明天雨该停了,晨光会轻柔地洒在松枝之上。
清晨的寒意渗入花骨,即便风势萧萧,牡丹仍能傲然挺立。
正午时分,花朵开得最为艳丽,盛放的姿态恰似舒展的笑颜。
夕阳西下,花瓣缓缓收拢,依旧顾惜着自身清雅的风姿。
可这清雅的风姿终究难以长久,后天或许就会有东风袭来。
这组诗是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三月,在黄州天庆观看牡丹所作。
苏轼的这三首牡丹诗,以牡丹的境遇流转为脉络,依次描摹雨中、晴日、凋零三种情态,字里行间满含赞花、爱花、惜花的赤诚之情,既各自成篇又浑然一体。
首章聚焦雨中牡丹,雨丝如雾似烟并非倾盆之势。“雾雨不成点,映空疑有无”的景致里,雾雨拂面却不见雨痕,花瓣凝满晶 莹水珠,红者鲜亮、白者幽香。时近黄昏雨雾渐浓,花叶缀满水珠低垂欲倾,如盼人扶持,这一笔将花的娇弱与情意相融,让情景浑然一体、物我难分,瞬间烘托出全诗意韵。
次章转而畅想雨过天晴的牡丹,诗人遥想“明日雨当止,晨光在松枝”的景致,以朝、午、暮三时铺陈花姿:晨雾缭绕松枝,牡丹伴着清芬端庄迎客;正午日照灼灼,花
这组牡丹诗以“花事流转”为暗线,脉络清晰且情感递进,既各有侧重又浑然一体。首章以雨为引、由景入花,将雨中牡丹描摹得鲜活传神;次章转向畅想,雨霁后的晴日牡丹景致明快动人,读来令人心旷神怡;末章则顺势延伸至花谢凋零的预想,从盛景过渡到衰态,满含深切惜憾。三首诗依次刻画雨中、晴日、衰败三种情态,完整呈现牡丹的风韵变迁,字里行间满是诗人对牡丹的由衷赞美与真挚爱怜。整诗笔触细致、刻画传神、抒情婉转,余韵悠长,让人回味无穷。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猜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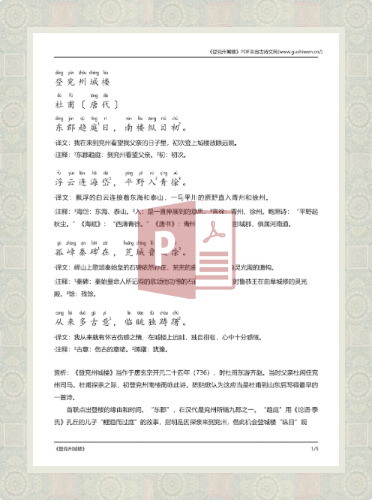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