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译文
先王破敌的石马已灰飞烟灭,外敌来犯的舰艇水鸟般遮天蔽海。亡国之祸就在目前,我击筑高歌,可有谁来相和?当年饮酒吟哦的风流文采之地,如今只见得列强的巨舰高帆巍峨。纵然失望于朝廷,我也难以放下经纶天地的壮志,总忘记不了要忠于我的君王。真无奈,闲居在这上海,心冷如灰,耳畔只有几声寒柝。
一箭传书便攻下聊城的功业,算起来还不如那呵手弄梅花的闲情呢。人在险途,好比在芦花上做巢的斑鸠,更别说什么读书养性的清欢生活。一个人独自沉吟,在月夜寒星下试拂我的佩剑,倚靠着屏风,那屏风上的花朵都摇摇欲坠。月光逐渐暗淡下来,即使在茫茫江滩眺望,也只能看到几点星星渔火。
注释
阿英(钱杏邨)所编之《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曾收此作,近人遂多谓其乃为甲午战争作。实误。叶恭绰据其所收藏之文廷式手稿,对此加按语云:“此感德人占胶澳事。原稿注:‘丁酉作。’”查德人侵占胶州湾正在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十月,而作者则于前一年二月被革职逐出北京,是年冬客居上海,故词题中有“岁暮江湖”之语。此与其所感之事的季节及其当时身为逐臣、流落江湖的处境,固完全相符。至于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之役,自当年中日战争初起至次年三月签订马关条约,作者仍在侍读学士任上,不会自称其“身在江湖”。
这是一首最能见作者的忧国之情、身世之悲,也最能见其风格特征的“感时抚
文廷式(1856—1904年),字道希、芸阁,号纯常子、罗霄山人等,江西省萍乡市城花庙前(今属安源区八一街)人,清咸丰六年丙辰十二月二十六日辰时(公元1856年1月21日)生于广东潮州,成长于官宦家庭,为陈澧入室弟子。中国近代著名爱国诗人、词家、学者,在甲午战争时期主战反和,并积极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是晚清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之一。1904年逝世于江西萍乡。

猜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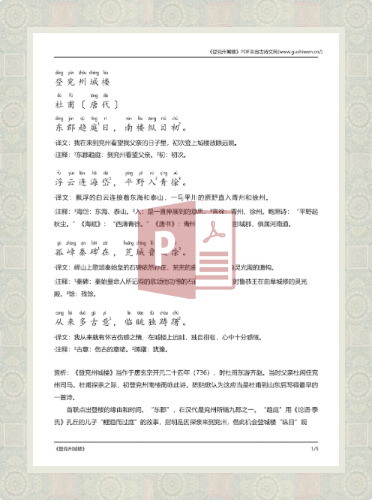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