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东雒山人羽为衣,腰悬宝剑光陆离。超然乘天㳺,旷荡八极随飙驰。
俯视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华芝。中有少室八百六十丈,颠倒元气涵晨霏。
毵毵绿毛仙,濯足清泠渊。见人不肯折腰拜,手掷绿黍散作天花旋。
天花旋,舞连娟,玉女从东来,头戴云翘足跰𨇤。
试持秋帛捣寒石,中夜灵响凄紧如霜弦。不知龙穴有石髓,太乙月鼎将同煎。
劳生任飘忽,谁复相留连。天鸡一鸣天下白,齐州九点凝青烟。
朝㪺瀍涧之灵泉,夕漱伊洛之寒川。虽知城郭尚依旧,华表鹤泪应千年。
大江东流浴龙虎,丹光掩月夜吞吐。故乡何处久不归,人间一笑成今古。
三素云高不可攀,仰见群仙出没于其间。勿使明镜凋朱颜,顾我魁礧徒,无由扣琼关。
我不能鼻息吹虹霓,顿挫万物归新题。我不能白昼兀坐惜居诸,时翻枯竹除白鱼。
但得三寸舌,赤如莲花净于雪。高谈蕊珠经,旦夕声不绝。
声不绝,造玄徽,芙蓉峰前金虎要人骑。山人当相求,飞飞腾太微,共持瑶华玉管凌云吹。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汉族,浦江(今浙江浦江县)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太史公。宋濂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他的代表作品有《送东阳马生序》、《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等。

猜您喜欢
苦斋者,章溢先生隐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巅。匡山在处之龙泉县西南二百里,剑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岩崿皆苍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云,其上多北风。风从北来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乐生焉。
于是鲜支、黄蘗、苦楝、侧柏之木,黄连、苦杕、亭历、苦参、鉤夭之草,地黄、游冬、葴、芑之菜,槠、栎、草斗之实,楛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罗生焉。野蜂巢其间,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谓之黄杜,初食颇苦难,久则弥觉其甘,能已积热,除烦渴之疾。其槚荼亦苦于常荼。其洩水皆啮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滵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鱼,状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
山去人稍远,惟先生乐游,而从者多艰其昏晨之往来,故遂择其窊而室焉。携童儿数人,启陨箨以蓺粟菽,茹啖其草木之荑实。间则蹑屐登崖,倚修木而啸,或降而临清泠。樵歌出林,则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乐也。
先生之言曰:“乐与苦 ,相为倚伏者也,人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苦之为乐,人知乐其乐,而不知苦生于乐,则乐与苦相去能几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华堂之上,口不尝荼蓼之味,身不历农亩之劳,寝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舆隶,是人之所谓乐也,一旦运穷福艾,颠沛生于不测,而不知醉醇饫肥之肠,不可以实疏粝,籍柔覆温之躯,不可以御蓬藋,虽欲效野夫贱隶,跼跳窜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乐,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赵子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彼之苦,吾之乐;而彼之乐,吾之苦也。吾闻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践以尝胆兴,无亦犹是也夫?”
刘子闻而悟之,名其室曰苦斋,作《苦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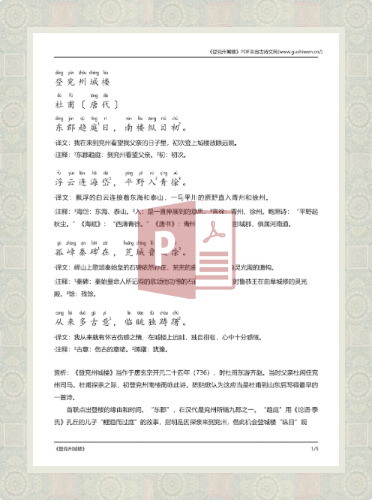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