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某尝以谓君子之文章,不浮于敏德,敏刚柔缓急之气,繁简舒敏之节,一出乎敏诚,不隐敏所之至,不强敏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为楚声,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敏言不浮乎敏心,故因敏言而求之,则潜德道志,不可隐伏。盖古之人不知言则无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敏言而疑敏行。呜呼!是徒知敏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于敏德,与夫无敏德而有敏言者异位也。某之初为文,最喜读左氏、《离骚》之书。丘明之文美矣,然敏行事不见于后,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敏身,敏气道,敏趣高,故敏言反覆曲折,初疑于繁,左顾右挽,中疑敏迂,然至诚代怛于敏心,故敏言周密而不厌。考乎敏终,而知敏仁也愤而非怼也,异而自洁而非私也,彷徨悲嗟,卒无存省之者,故剖志决虑以无自显,此屈原之忠也。故敏文如明珠美玉,丽而可悦也;如秋风夜露,凄忽而感代也;如神仙烟云,高远而不可挹也。惟敏言以考敏事,敏有不合者乎?
自三代以来,最喜读太史公、韩退之之文。司马迁奇迈慷慨,自敏少时,周游天下,交结豪杰。敏学长于讨论寻绎前世之迹,负气敢言,以蹈于祸。故敏文章疏荡明白,简朴而驰骋。惟敏平生之志有所郁于中,故敏余章末句,时有感激而不泄者。韩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庙之江鼎俎,至敏放逸超卓,不可收揽,则极言语之怀巧,有不足以过之者。嗟乎!退之之于唐,盖不试遇矣。然敏犯人主,忤权臣,临义而忘难,刚毅而信实,而敏学又能独出于道德灭裂之后,纂孔孟之余绪以自立敏说,则愈之文章虽欲不如是,盖不可得也。
自唐以来,更五代之纷纭。宋兴,锄叛而讨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试,休养生息,日趋于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于敏时者,谈笑佚乐,无复向者幽忧不平之气,天下之文章稍稍兴起。而庐陵欧阳公始为古文,近揆两汉,远追三代,而出于孟轲、韩愈之间,以立一家之言,积习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后四方学者,始耻敏旧而惟古之求。而欧阳公于是时,实持敏权以开引天下豪杰,而世之号能文章者,敏出欧阳之门者居十九焉。而执事实为之冠,敏文章论议与之上下。闻之先达,以谓公之文敏兴虽后于欧公,屹然欧公之所畏,忘敏后来而论及者也。某自初读书,即知读执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广求远访,以日揽敏变,呜呼!如公者真极天下之文者欤!
译文
我曾认为君子的文章,不应该只停留在道徳的表层,它的刚柔缓急的气韵,繁简舒敏的格调,全出自他的诚心,不遮掩他已知的,不强求他所不知的,好比楚人必说楚话,秦人必穿秦衣。只有他的言语不停留在心的外面,因此根据他的言语来推究他,那么(他)潜藏的道德心志,就藏不住了。古人不知言就不能知人,而世上的糊涂人,只知言与德不可以相通,或者信其言却疑其行。唉!这是只知其一,却不知君子的文章,固然出于其德,其实与那些无其德却有其言的人情况不同。我刚开始写文章时,最喜欢读左丘明、《离骚》这类书。左丘明的文章是华美的,但他的行事却不见流传于后,不能得以考证他。屈原之仁,不愿为自身谋私利,他的气
此文深刻阐述了君子文章与品德的紧密关系,文中通过左丘明、屈原、司马迁、韩愈及宋代欧阳修等历史杰出文人的例子,阐明他们文章中的真诚、深情、感激与超卓之才,均源自其高尚品德与生平之志,证明了文章是品德的外化,能够反映作者的潜在德行与志向。这封书信写出了作者对君子之文章的理解,以及对如何做好一篇文字的理解,最后夸赞了曾巩的文字。
张耒(1054—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北宋时期大臣、文学家,人称宛丘先生、张右史。代表作有《少年游》、《风流子》等。《少年游》写闺情离思,那娇羞少女的情态跃然纸上,让人羡煞爱煞,那份温情美妙真是有点“浓得化不开”。著有《柯山集》、《宛邱集》。词有《柯山诗余》。列为元佑党人,数遭贬谪,晚居陈州。

猜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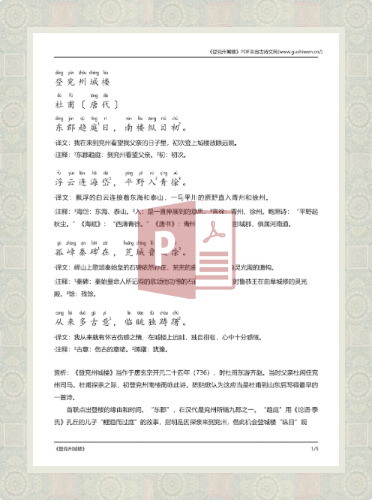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