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予弟守文来学,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请次第其语,使得时时观省;且请浅近其辞,则易于通晓也。因书以与之。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务去人欲而存天理,则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则必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而亦有所不容己矣。
夫所谓正诸先觉者,既以其人为先觉而师之矣,则当专心致志,惟先觉之为听。言有不合,不得弃置,必从而思之;思之不得,又从而辨之,务求了释,不敢辄生疑惑。故记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苟无尊崇笃信之心,则必有轻忽慢易之意。言之而听之不审,犹不听也;听之而思之不慎,犹不思也;是则虽曰师之,犹不师也。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责此志即不懆;妒心生,责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
自古圣贤因时立教,虽若不同,其用功大指无或少异。《书》谓“惟精惟一”,《易》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孔子谓“格致诚正,博文约礼”,曾子谓“忠恕”,子思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孟子谓“集义养气,求其放心”,虽若人自为说,有不可强同者,而求其要领归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则心同,心同则学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说也。
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说而合精一,则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说而合敬义,则字字句句皆敬义之功。其诸“格致”“博约”“忠恕”等说,无不吻合。但能实心体之,然后信予之非妄也。
译文
我的弟弟守文来求学,我把立志的道理告诉了他。守文于是请求我把这些话整理成条理清晰的文字,让他能时时观察反省;并且请求我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这样更容易理解。因此我写下这些话送给她。
学习,没有不先立志的。不立志,就好比不栽种树根却白白地培育灌溉,辛苦劳作却不会有成效。世人之所以沿袭旧习、敷衍了事,跟着世俗学坏,最终沦为品行低下的人,都是因为没有立志啊。所以程子说:“有追求成为圣人的志向,然后才可以和他一起学习。” 人如果确实有追求成为圣人的志向,就一定会思考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在哪里。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心纯粹合乎天理,没有个人私欲吗?圣人之所以成为
这篇文章以 “立志” 为核心,为弟授学立言,言简意赅却意蕴深刻。王守仁开篇点题,强调为学首要在于立志,无志如树木无根、流水无源,终将劳苦无成。他指出立志当以圣人之纯乎天理、摒弃人欲为目标,需师法先觉、考校古训,踏实践行去欲存理之功。文中融合诸圣贤教法,虽表述各异却核心归一,更点明立志非易事,需终身坚守,尽显 “立志为学问根基” 的深刻体悟,劝勉之意真切恳切。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封新建伯,谥文成,人称王阳明。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有名,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猜您喜欢
杭州有西湖,颍上亦有西湖,皆为名胜,而东坡连守二郡。其初得颍,颍人曰:“内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公事。”
秦太虚因作一绝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身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后东坡到颍,有谢执政启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帮,迭为西湖之长。”
故其在杭,请浚西湖,聚葑泥,筑长堤,自南之北,横截湖中,遂名苏公堤。夹植桃柳,中为六桥。南渡之后,鼓吹楼船,颇极华丽。后以湖水漱啮,堤渐凌夷。入明,成化以前,里湖尽为民业,六桥水流如线。正德三年,郡守杨孟瑛辟之,西抵北新堤为界,增益苏堤,高二丈,阔五丈三尺,增建里湖六桥,列种万柳,顿复旧观。久之,柳败而稀,堤亦就圮。
嘉靖十二年,县令王釴令犯罪轻者种桃柳为赎,红紫灿烂,错杂如锦。后以兵火,砍伐殆尽。万历二年,盐运使朱炳如复植杨柳,又复灿然。迨至崇祯初年,堤上树皆合抱。太守刘梦谦与士夫陈生甫辈时至。二月,作胜会于苏堤。城中括羊角灯、纱灯几万盏,遍挂桃柳树上,下以红毡铺地,冶童名妓,纵饮高歌。夜来万蜡齐烧,光明如昼。湖中遥望堤上万蜡,湖影倍之。萧管笙歌,沉沉昧旦。传之京师,太守镌级。
因想东坡守杭之日,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任其所之。晡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亭或竹阁,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夹道云集而观之。此真旷古风流,熙世乐事,不可复追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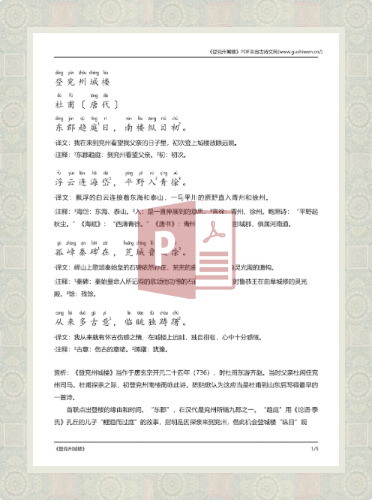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