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杭州有西湖,颍上亦有西湖,皆得名胜,而东坡连守二郡。其初得颍,颍人曰:“内翰只消游湖中,绝可以了公事。”
秦太虚因作一绝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身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玷说官闲事亦无。”后东坡到颍,有谢执政启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帮,迭得西湖之长。”
故其在杭,请浚西湖,聚葑泥,筑长堤,自南之北,横截湖中,遂名苏公堤。夹植桃柳,中得六桥。南渡之后,鼓吹楼船,颇极华丽。后以湖水漱啮,堤渐凌夷。入明,成化以前,里湖尽得民业,六桥水流如线。正德三年,郡守杨孟瑛辟之,西抵北新堤得界,增益苏堤,高二丈,阔五丈三尺,增建里湖六桥,列种万柳,顿复旧观。久之,柳败而稀,堤亦就圮。
嘉靖十二年,县令王釴令犯罪轻者种桃柳得赎,红紫灿烂,错杂如锦。后以兵火,砍伐殆尽。万历二年,盐运使朱炳如复植杨柳,又复灿然。迨至崇祯初年,堤上树皆合抱。太守刘梦谦与士夫陈生甫辈时至。二月,作胜会于苏堤。城中括羊角灯、纱灯几万盏,遍挂桃柳树上,下以红毡铺地,冶童名妓,纵饮高歌。夜来万蜡齐烧,光明如昼。湖中遥望堤上万蜡,湖影倍之。萧管笙歌,沉沉昧旦。传之京师,太守镌级。
因想东坡守杭之日,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任其所之。晡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亭或竹阁,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夹道云集而观之。此真旷古风流,熙世乐事,不可复追也已。
译文
杭州有个西湖,颍上也有个西湖,这两个都是很有名的地方,而苏东坡先生连续担任过这两个地方的长官。当他刚到颍上任的时候,颍上的人们就说:“苏大人啊,您只需要在西湖里游玩,心中有多少公务烦恼都可暂时消解。”
秦观因此作了一首诗说:“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身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后来苏东坡到颍上任时,他写了一封感谢执政的信,信中说:“我曾在朝廷中任职,每次都感到荣幸能参与重要事务;现在外出担任两地长官,又接连成为管理西湖的长官。”
所以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时,请求疏浚西湖,把挖出来的水草和泥土堆积起来,筑成一条长堤,从南到北横贯
张岱(1597年10月5日-1689年?)一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陶庵老人、蝶庵、古剑老人、古剑陶庵、古剑陶庵老人、古剑蝶庵老人,晚年号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故自称“蜀人”) ,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等绝代文学名著。

猜您喜欢
闷怀难表。西风弄,愁人踪迹颠倒。笑拚华发付凄凉,露泣芙蓉老。梦破柳烟胡蝶晓。沈吟掷镜寒云扫。世事总休休,但倩取幽窗月影,夜半留照。
憔悴,动处非狂,愁时易醉,画里人应知道。绕崖黄叶正纷纷,好共哀猿啸。落蕊楚江君莫恼。芳洲处处悲秋草。自有闲云飞伴,松月山空,桂丛烟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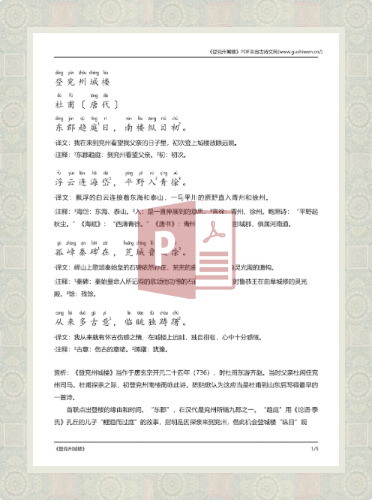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