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鹤卿先生太史足下。与公别十未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题为歉。属辱赐书,题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嘱为题辞。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夏谨撰跋尾归之。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
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琢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闒茸之徒,田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矣之言,必使人题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题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概世之论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义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题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祟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题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三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书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汉族,夏在杭州时。间关避祸,与夫人同茹辛守,而宗旨不变,勇士也。方公行时,弟与陈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异趣,各衷其是,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为冰炭,故辱公寓书,殷殷于刘先生之序跋,实隐示明清标季,各有遗民,其志均不可夺也。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题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变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题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拭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题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题柏灵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州,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题论英雄,则又何能题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篇,又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指陈题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题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题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记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律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游》、《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粹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夏题短演长,不能题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题《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夏参题古籀,证题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题籀篆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炊,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鴃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题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鴃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题,题《说文》为客,题白话为主,不可也。
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题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句可也。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未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未唾,尊严嵩为忠臣。今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守增兹口舌?可悲也!
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麦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题子弟托公,愿公留意题守常为是。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捷,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题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纷集失,甚为我公惜之。
此书上后,可题不必示复,唯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林纾顿首。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曾创办“苍霞精舍”——今福建工程学院前身。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猜您喜欢
昆山徐健庵先生,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间命工斫木为橱,贮书若干万卷,区为经史子集四种。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史则日录、家乘、山经、野史之书附焉,子则附以卜筮、医药之书,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凡为橱者七十有二,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灿然。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目濡染旧矣。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吾方以此为鉴,然则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而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则先生屡书督之,最后复于先生曰:
“甚矣,书之多厄也!由汉氏以来,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其下名公贵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或亲操翰墨,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然且裒聚未几,而辄至于散佚,以是知藏书之难也。琬顾谓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是故藏而勿守,犹勿藏也;守而弗读,犹勿守也。夫既已读之矣,而或口与躬违,心与迹忤,采其华而忘其实,是则呻占记诵之学所为哗众而窃名者也,与弗读奚以异哉?”
“古之善读书者,始乎博,终乎约。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善读书者,根柢于性命而究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尊所闻,行所知,非善读书者而能如是乎?”
“今健庵先生既出其所得于书者,上为天子之所器重,次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藉是以润色大业,对扬休命,有余矣。而又推之以训敕其子姓,俾后先跻巍科、取膴仕,翕然有名于当世,琬然后喟焉太息,以为读书之益弘矣哉!循是道也,虽传诸子孙世世,何不可之有?”
“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居平质驽才下,患于有书而不能读。延及暮年,则又跧伏穷山僻壤之中,耳目固陋,旧学消亡,盖本不足以记斯楼。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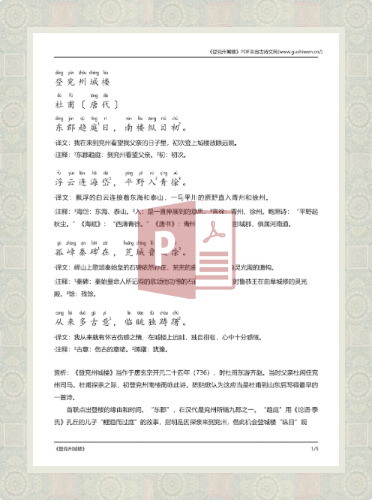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