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译文
永贞元年九月被贬永州,如今北归四千里,终于从永州回到长安。
朝廷下诏准许于暖春返京,回途官道两旁,新花处处开放。
注释
灞亭:灞水边上的驿亭。灞水在长安城东二十里,驿亭是古代供行旅途中休息的地方。
十一年前:指公元805年,诗人被贬离开长安的时间。
南渡:指被贬到永州。
四千里外:永州北距长安约四千里。四千里:《旧唐书·地理志》:“江南西道永州,在京师南三千二百七十心里。”这里说“四千”,是举其成数。
许:许可。
逐:跟随。
阳和:暖和的春天。
驿路:官道,古时供传车、驿
诗人曾被贬永州十一年,相隔四千里之遥,如今终得北归。诗的开篇两句“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看似是对过往经历的平实陈述,实则凝练地裹藏着复杂而激动的情愫——既有当年遭贬的愤懑,也有对漫长放逐生活的追忆,更有重回长安的难掩欣喜,百感交集于朴素字句间,反倒让抒情更具感染力。
后两句“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则借沿途景致抒发回京路上的畅快心境。朝廷下诏准许他在暖春时节返京,驿道两旁新花处处绽放,这明媚春光与鲜活花景既是眼前实景,更是他内心状态的投射。即将踏入长安城门的他,满心激动与喜悦却不直白言说,仅以“处处新”三字暗表心意:既写花的清新鲜活,更写人的轻快
《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是一首七言绝句,为一首抒发回京喜悦之情的诗。此诗前二句叙写诗人遭贬和被召回来的情景,后二句写他在回京的路上所见的景物。整首诗以景结情、景中寓情,既是写花,更是写人,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胜过万语千言。
柳宗元(773年~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人,出身河东柳氏,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被贬永州期间,居所附近有愚溪,人称“柳愚溪”。后官终柳州刺史,世人称“柳柳州”。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章的成就大于诗作。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被推为“游记之祖”。著有《河东先生集》。

猜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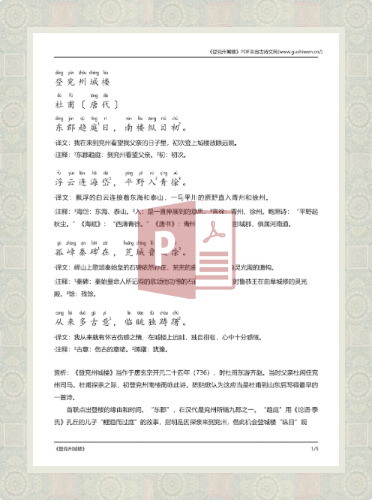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