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始的播放列表项


黄山笔冢连糟丘,墨池酒泉相映流。霜毫画酣玉薤露,云笺夜酗蒲萄秋。
黄山中人鹖冠子,身裹绿萝著双履。萧洒唯应继右军,濩落偏能如长史。
山人草圣自豪雄,何事栖迟酩酊中。年过五十无名位,其奈萧然沧海东。
砚屏颠倒乌皮几,落日垆头睡初起。向壁凭陵小吏惊,据床挥霍郎官喜。
七闽大姓五陵儿,握粟持金岂顾之。心同气合即挥洒,归卧山中无所为。
想当脱腕临池处,兴入寥天与神遇。深沈铁绠锁寒蛟,偃蹇乌藤絓高树。
鱼丽云鸟势萦纡,疑是将军破骨都。骖麟翳凤何飘忽,倏忽仙游蕊珠阙。
又如祇苑说空禅,灵花历乱迷诸天。离丽落磊千万态,流水行云皆自然。
醒来不记濡头墨,千尺寒涛照眼白。淮海仍传宝晋风,长沙复见藏真迹。
黄山茆宇思悠悠,柿叶青青覆酒楼。白头未遂中书贵,风流亦似醉乡侯。
王恭(1343-?),字安仲,长乐沙堤人。家贫,少游江湖间,中年隐居七岩山,为樵夫20多年,自号“皆山樵者”。善诗文,与高木秉、陈亮等诸文士唱和,名重一时。诗人王 曾为他作《皆山樵者传》。明永乐二年(1404年),年届六十岁的王恭以儒士荐为翰林待诏,敕修《永乐大典》。永乐五年,《永乐大典》修成,王恭试诗高第,授翰林典籍。不久,辞官返里。王恭作诗,才思敏捷,下笔千言立就,诗风多凄婉,隐喻颇深。为闽中十才子之一,著有《白云樵集》四卷,《草泽狂歌》五卷及《风台清啸》等。

猜您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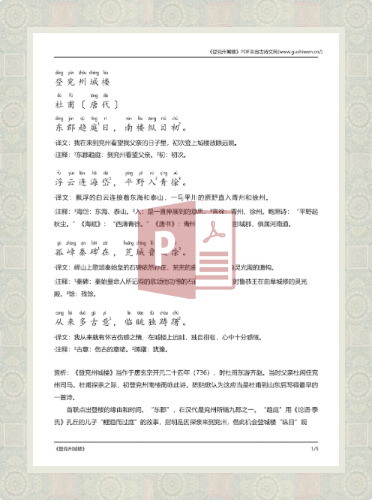
 下载PDF
下载PDF
 查看PDF效果
查看PDF效果
